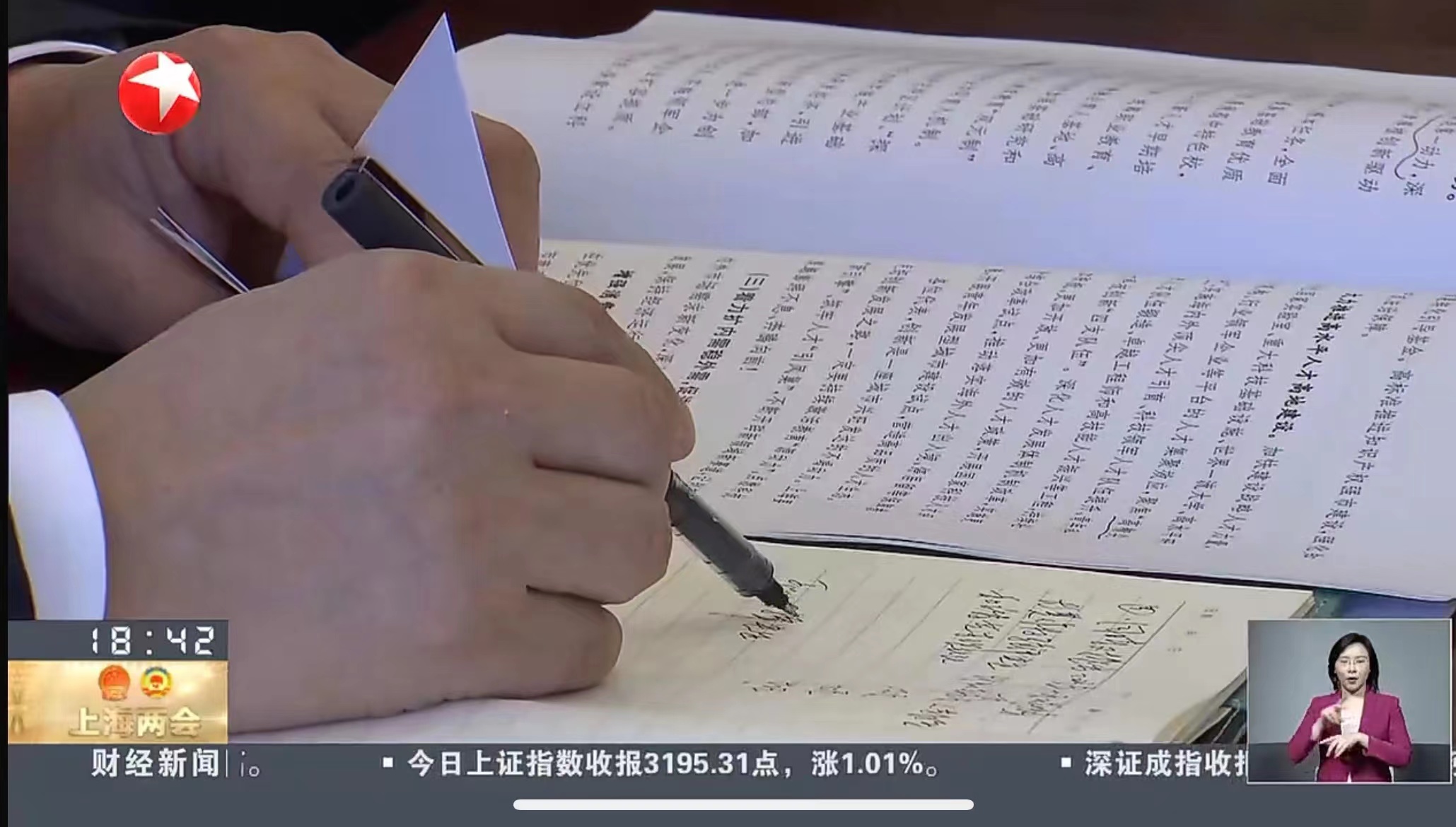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快速流变的数字化和媒介化社会中,“媒介”逐渐成为传播理论关注的焦点,媒介理论研究也成为了传播研究这10年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周好雨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2期刊文,发现近10年来,围绕媒介本体的重新定义、物质性研究、媒介化理论、媒介与身体以及媒介理论的其他分支方向,学者们展开了富有想象力但缺少共识的讨论。尽管新理论、新概念和新方法不断涌现,传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但媒介理论仍然需要更多经典的研究和深入的对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短短10年间,远程教育、智慧医疗、移动支付、共享出行、网络零售、电商直播等数字化生活方式和信息服务渐次进入现实,构成了新时代国人生活的日常图景。在快速流变的数字化和媒介化社会中,“媒介”逐渐成为传播理论关注的焦点,媒介理论研究也成为了传播研究这10年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其成长速度可以用“狂飚突进”来形容。
这一方面当然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臻完善息息相关——互联网基础设施具有如此重要的行动力,以至于它以无限可能的方式填充、宰制、重构人们的生活。
另一方面,这也与媒介被抽象化后爆发出的想象力有关。媒介被视为一种“居间”的隐喻,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哲学思考。有学者将这种“居间”看作是创造两端的起点,从而形成了媒介本体论的思想。也有学者反对媒介的天然先在性,认为本体论会造成一种“有”或本质主义的错觉,媒介的居间性是一种“无”,只有当媒介物处于居间位置之时,媒介的意义才会生成。
不过,不管在媒介哲学上存在什么分歧,“重识媒介”和建设媒介理论的知识体系已经不可避免,传播学正在将“媒介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陈词滥调抛到一边,面对“人与媒介的相接相嵌”的现实,步入“媒介入射角”的时代。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为了更精确地描述10年来媒介研究的发展进路,研究者将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的量化方法和文本深度阅读的质化方法相结合,分析了党的十八大至党的二十大的10年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CSSCI核心期刊的相关文本。
从关键词共现网络时区图所展现的情况来看,每一个阶段的关键词都有所不同,这说明媒介理论正处于“生成”的状态。在本研究采样时段之初,“媒介化”就呈现出极强的高凸显性,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媒介到底是什么”的重思,对作为一种媒介理论视角的“物质性”的集中讨论,也于2014年首次出现。从共现关系来看,在后来学界对“媒介融合”“空间”“具身”“元宇宙”等关键词的研究里,对“媒介化”持续讨论在不断深入。
2016年由于网络直播平台数目激增被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这也意味着我国移动传播发展到了新的阶段。移动终端的普及改变了传播的社会情境,“空间”问题于次年成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同样在2016年,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带来大量关于深度媒介化如何重塑人类存在方式的讨论。作为一种新传媒技术,虚拟现实在传播实践中的持续应用让学者们注意到传播与身体关系的变化。
2019年,学界开始对“具身性”进行集中阐释。但随着学界对媒介物质性的持续讨论,尤其在2020年“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观念被提出后,“具身性”一词的媒介本体论意涵渐渐凸显,于是学者们在传播研究中重提“身体”概念,用以指有血有肉的、“作为身体的我”,同“媒介技术的具身”加以区分。
10年来,媒介本体论、物质性、媒介化理论、媒介与身体等问题,不断成为传播学者们讨论的焦点。
从媒介实体论到媒介本体论
媒介理论的起步与学界提倡重新理解“媒介”概念有莫大关联。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传播学者已基本都熟悉麦克卢汉和他的《理解媒介》。然而现在看来,虽然当时大家常提及麦克卢汉,但并不真正理解媒介。即使今天,我们开始尝试用麦克卢汉的隐喻视角去理解媒介,却又常常发现:其实我们也并不理解麦克卢汉。
长期以来,中国传播学者理解的媒介是美国传播学植入的媒介观,即组织化、专业性和生产内容的功能性“实体”。这不仅因为美国传播学的话语霸权,也因为它更符合人们看到的常识。许多传播研究者认为媒介就是一个可以被全面认识的实体、一个实体化的媒介组织,于是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常识,并被常识所建构。
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这种媒介认识论仍深刻影响着中国学者。彼时,国内传播学界会把任何与媒介组织有关的话题都当作是传播研究,而把任何与媒介组织无关的现象都当作与传播无关的事。其结果就是,我们把在建筑工地上使用的石头和在街上争吵时使用的石头当作了一样的东西。然而,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媒介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自我意识与面向世界的意向性,毕竟“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是受之影响,抑或要避之影响,都值得剖析”。传播学者终于开始区分建筑工地上使用的石头和在街上争吵时使用的石头。
从理论抽象的角度来看,隐喻是一种比实体化更合适的方法论。胡翼青提出:对传播学研究而言,在方法论上把媒介理解为一个抽象的隐喻,是一个更具整体性的视角,从而找寻到真正属于传播学的研究问题,并重塑学科气质。
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化,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将先前所有用来表征和交流的媒介通通融合在二进制的平台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媒介视为整体。因为在复杂社会关系中,媒介已经成为一个集合体,并以这种整体的存在作用于人的感知,影响着人之所以为人的方式。按照彼得斯的说法,即媒介是“任何处于中间位置的因素”(In Medias Res),不仅是“表征性货物”(symbolic freight)的承运者(carriers),而且也是一种容器或环境,是人类存在的塑造者(crafters)。如钱佳湧所说:媒介之为“媒介”的本质,在于它在自身之内敞开了一种富于意义的空间,使人、技术、权力、资本等传播所牵涉的要素在此交汇融通,共同构成一个“行动的场域”(fields of action)。所以在本体论意义上,媒介很可能暗含某种日趋连贯的整体性逻辑,具身性、可见性、可供性等一系列新概念开始作为媒介性内涵的组成部分,得到讨论。在可被预见的未来,对共通的媒介性的研究将成为媒介本体论中愈发重要的命题,给予“复数形式而非单数形式的媒介理论”以统合的可能。
媒介的物质性与基础设施媒介
传播学建制化过程中的导向性,让媒介的物质性长久地被隐蔽在功能主义的工具性之下,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但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彻底颠覆了大众传媒时代的技术逻辑,物质性的讨论变得不可避免。因为,从物质性角度进一步发展技术、身体、空间等媒介理论,能回应媒介的现实建构问题。
我国学者对媒介物质性的讨论,起初更多是将媒介视为影响现实生活与生存的“背景”,强调构成媒介的质料、物质、技术如何限定具体的传播实践和场景。复旦大学一批学者发起的城市传播研究,便是以物质性的视角参照数字技术下的新型城市生活。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者充分探讨了城市的物理空间与物质设施如何组织、安排、调节城市的日常生活,并赋予其特定的时空节律,同时也解蔽了虚拟赛博空间所依赖着的光纤、计算机、服务器等物质性基础设施,认为城市是具有动能的物质体系、是实体化的基础设施媒介。在数字媒介快速发展的今天,媒介的物体系以技术载体的形式重构了社会的业态和生活方式,我们无法想象失去网购、外卖服务、共享单车的生活,不得不承认这些技术元素已经像水、电、天然气、公交工具一样成了我们社会的基础设施。更进一步,当二进制成为当下交往空间的最基本构成元素,一种全新的、跨越虚实边界的数字化生存和交往方式,也在这种数字化技术的基础设施之上逐渐成型。
基础设施媒介展现出了媒介的另一面,正像“基础设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静默无言,低调回避。这似乎也是媒介的一贯表现和一般品质——为了彰显别的人或事而将自己遮蔽隐藏起来”。媒介既可以有万人瞩目的外观,也可以成为像基础设施那样完全透明却又无处不在的背景。正像克莱默尔所说的那样:“传媒的作用就像玻璃窗:它越是透明,越是在我们的注意阈之下不引人注目,它就越是更好地完成任务……只有当传媒的有效作用受到干扰的时候,或者传媒崩溃的时候,传媒自身才被我们想起。”这种现象被现象学的学者高度关注,比如唐伊德就将之称为媒介与人的具身关系。
媒介具身性体现出了媒介物的独特性,而国内学者显然关注到了媒介技术在传播中的退场和隐身。如芮必峰和孙爽认为,媒介并非外在的客观对象,而是内在于人的知觉体验的具身化的现象媒介。杜丹则认为,媒介物的中介化过程有赖于其“上手”且“透明”的意向,只有当媒介物“变得‘退出’(withdrawal)、透明或‘延伸’”,人的具身化实践才能持续进行。而胡翼青和赵婷婷则评价说:一方面经由庞大媒介技术体系中介的传播无处不在,另一方面人们却怎么也“看不到”媒介技术本身。这一对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使媒介技术体系本身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幽灵。
媒介化研究的多元取向:表征、建构和自我生成
在我国的媒介化研究中,越来越多学者看到了“物质性”取向的媒介化。这和我们前文叙述过的媒介物质性研究——基础设施媒介的发掘有深刻联系。数字媒介作为一种新的结构社会的力量,其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与以往任何一种“旧”媒介不同:它下沉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赫普将这种能力称为“深度媒介化”。陈昌凤在论述社会的深度媒介化时说:如今的社会交流中,人类依赖的中介不是内在的精神现实,而是基于发生在技术平台、媒介体系上的交流和意义的建构。
也有学者把媒介化理解为社会的可见性问题,即如何更容易实现内容在媒介上的可见度、如何设定议程等,如舒尔茨试图将媒介改变交流与互动的过程归纳为四种类型。对此,戴宇辰认为,舒尔茨虽意识到媒介逻辑深刻影响社会现实,但他所描述的“媒介化”仅仅体现出了媒介的呈现性。这种“媒介化”观念中的媒介,只是一种广义社会环境改变的代理者。
从“作为媒介性的生成性”视角观照当今世界的深度媒介化现实,我们会发现:作为基础设施媒介的技术逻辑,二进制的本质就是让人与物在相遇之中不断发生新的意义、不断生成新的媒介,所以深度的媒介化就是媒介在生成媒介。在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本身就是世界。
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从虚拟现实到元宇宙
深度媒介化时代,人的存在方式、主体意识和人与世界的关系也被媒介重塑了。李沁认为,人与媒介的关系会经历从“内”、“外”到“合”的三个“媒介时代”。这样的描述似乎暗示了一种由彼此区隔到互相嵌入的关系转变,似乎人和媒介都重又被物化为某种可感的实体。而传播研究领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的确是从重新理解“身体”开始的。
“讨论传播中的身体,必须回到麦克卢汉。”当学者们在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中重新定位身体时,首先意识到的就是作为“义肢”的技术延伸了人原本的身体。VR是现代计算机技术支撑起来的数据化空间,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纯粹的信息。但这种虚拟手段,并非简单的形式模拟,而是要让使用者通过媒介技术获得与在外界物理空间或理想化幻觉空间中等同的感官体验。孙玮认为,不同于基于媒介技术的“模拟身体”,数字技术通过算法技术转化与生成具有高度解析性的“数据躯体”,实现作为主体的人在赛博空间内外的拓展,是“再造身体”。
杨慧、雷建军在对国外研究的VR特征进行归纳时发现了两个核心概念:沉浸(immersion)与在场(presence)。前者指用户的卷入程度,后者指用户的共在感知。为凸显传播效果研究中身体及其知觉类型系统性的缺席,刘海龙和束开荣提出,“必须承认身体在信息流动与接受过程中扮演着的物质论地位”,以具身观念反观新传媒技术及其实践,奠定了以“具身性”观念解蔽和强调被技术遮盖的身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的认知。近年来出现的“人肉搜索”“跨境代购”等都属此类具身传播实践,研究者应进一步探讨身体如何将人与技术连接在一起,同时作为辅助技术系统的“补丁”和干扰网络秩序的“病毒”而存在。
2021年,“元宇宙”概念横空出世,学者们对人-技术媒介-社会与世界关系的复杂变化的讨论更为激烈。陈昌凤认为:元宇宙逻辑将进一步改变交流的性质和人类的社会关系,它的价值观挑战着人的自主性与数字化人格和尊严。元宇宙声称提供一种摆脱物质存在的自由,唤醒人类驾驭抽象事物的深层心智能力,但其本质是媒介技术利用对人类大脑的感官刺激来实现自身扩展。骆正林和白龙以柏拉图洞穴寓言类比,认为元宇宙中的人就像“数字洞穴”中的囚徒,被束缚在自我思想的阴影和唯我观中,逐渐丧失知觉真实的能力。
认识论的延展:媒介地理学与媒介考古学
当媒介的意象与时间和空间交汇,就形成了两个特别有趣的边缘学科:媒介地理学和媒介考古学。10年来,这两个边缘领域吸引了许多媒介研究者的目光,甚至超过了对媒介社会学和媒介生态学的关注。
袁艳通过对德国古典地理学的思想史考察,提出古典地理学与传播学“本是同根生”的见解。
随着新技术的迭代,空间作为媒介的体验与实践渗透在人类对日常生活的感知和想象中,空间媒介化的特征和作用日益显化,呈现出奇妙而丰富的人文与社会内涵。目前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多为对其思想史和合法性的描述,然而,大规模经验研究的可能性已经显现。如张昊臣通过研究3种不同的制图方式发现:位置媒介能够杂合外部、内部、俯瞰视角与地面、技术、叙事视角,营造出具有流动、拼接、歧异等特征的新场所经验,这提示了由制图学视角重审媒介与城市关系的可能性。许同文关注到了自我追踪与移动技术关联可以促成不同的数据实践。他以“运动世界校园”APP为例,发现:由于媒介技术自身具有的媒介特性,在不同场景中,人与非人的因素通过位置媒介相互勾连,会形成殊异的数据实践。
在关涉到时间维度的媒介研究中,媒介考古学打开了一条历史想象的路径。施畅梳理出媒介考古学兴起的电影考古学和德国媒介理论两条主干。
学者袁艳重审手账这一“慢媒介”的流行,发现年轻人从手账中感知到的“慢”和“断”并非反数字化的书写动作或“纸笔”的固有属性带来的,而是传统书写技术和数字化书写等技术之间、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生成、转化的结果。通过人和社会不间断的媒介化,技术、社会的流变形成了某种复杂的连续性,其背后甚或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权力关系变化。但要注意的是,“媒介考古学”对“媒介”的定义不能过于零散,不然便会沦为对主流历史的边角补充。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迅速崛起,中国传播学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结构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媒介研究思路,并为传播学的再度理论化提供了新的机遇。新理论、新概念和新方法不断涌现,传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当然,这些研究其实还在生成过程中,很少有深入的对话,有一些领域甚至还停留在理论介绍和历史描述的层面。所以,这狂飚突进的10年,相关研究还需要在内涵建设上更进一步,需要更多经典的回溯和深入的对话。
(载《传媒观察》2023年2月号,原文约12000字,标题为《狂飚突进的10年,中国媒介理论研究的嬗变》。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周好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