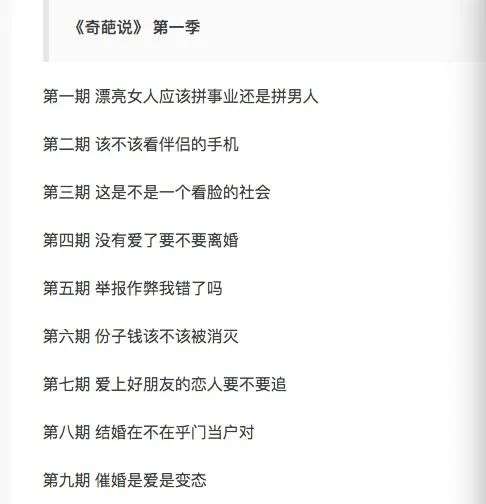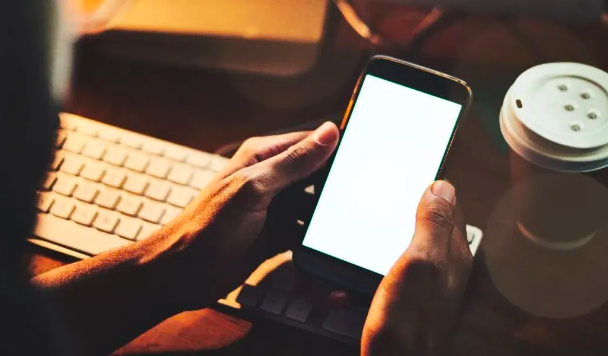《乘风破浪的姐姐》已经播出到第二季了,最新一期《奇葩说》的辩题还是“独立女性该不该收彩礼”。
并不是说“浪姐”本身表达了多么具有进步性的议题,但刚过去这一年,确实是借综艺轰炸之力,女性议题得以在线上全方位多角度讨论的一年。
综艺聚光灯之外,还有“拉姆案”、“散装卫生巾”和“假靳东骗局”等具体而又近距离的女性问题,无一不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大量公共讨论。
然而经过了这些种种,我们竟然还要听“欣赏与爱不应该分性别,美好的世界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这种空洞又委屈的说教式口号;还要看诸位在名利场沉浮能养活一家几口的“独立女性”,出来以身作则拒绝彩礼;还要假装自己不知道真的存在没有选择的女性,需要靠彩礼来为兄弟娶妻盖房;还要把女性独立选择的问题归为女性自我愿不愿意被贴标签,愿不愿意服从一个标准的问题。
这难免让人沮丧。
《奇葩说》作为一个综艺节目,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解决一系列需要靠法律法规来解决的问题。但它为什么不能提出一个更好的问题?
这个曾经靠提出和回答问题,让“边缘群体”被看见的节目,怎么到了今天就要假装去提出一个问题?
01 奇葩说变了,奇葩说没变
指出“《奇葩说》变了”似乎没有意义。
这是它作为网综存在的第七年了。在表达空间和受众因各种原因,都愈发“内卷”的内容制作语境里,没有一个靠表达为核心的综艺节目,能历经千帆又不坠青云。
节目组也无法假装无事发生。两年前《奇葩说》第五季出了个宣传片,调侃自己“IP老化、选手抱团、流量不行,评分下滑”,几乎想放弃治疗。后来几个年轻观众来到病床前,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
“你放弃治疗了,我们怎么办?”
“是谁教我养男人不如养一条狗的?是谁鼓励我一定要看男朋友手机的?”
“奇葩说,你不能放弃啊!”
看起来,“求变”,正是过去几季《奇葩说》的重要命题。这项工作进行到了第七季,老奇葩因为各种原因被冲散,各种语言类艺术表演者加入舞台,赛制改进,导师纳新。原先被诟病的“问题”似乎都被给出了解决方案。
但历季最低的豆瓣评分,证明了节目的质量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也证明了那些被总结为“病因”的问题可能只是表层“症状”。扬汤止沸,收效甚微。
第一季的《奇葩说》现场剧照
时间拨回到七年前的2014,《奇葩说》刚开播的第一季里,其实就有《漂亮女人应该拼事业还是拼男人》的辩题。这和今天的《独立女性应不应该收彩礼》异曲同工,都是基于一个传统、落伍的性别意识框架下延伸的两性问题,也都把女性面对的问题之复杂性和结构性,给片面化、二元化了。
但讨论这个问题在《奇葩说》刚开播的七年前是可以接受的,今天则不然。毕竟如果说过去这七年里,我们的公共生活还有任何算得上“进步”的部分,性别意识和性别议题的广泛讨论应该在这部分中占了相当大比例。
但《奇葩说》却选择忽略掉这个动态。
所以,与其说《奇葩说》的问题是“变化”带来的,不如说是它某种意义上的“不变”和“停滞”带来的。或者说,当问题的讨论随着时间一尺一尺往前推进和发展时,《奇葩说》作为一个辩论节目(如果是的话),并没有展现出与之相匹配的敏锐度和承载力。
这让几年前人们热议《奇葩说》在“娱乐性”和“进步价值”之间的取舍时,所给出的那一套马东“以退为进”叙事——即利用大众娱乐产品的覆盖性和穿透力,去影响更多人,而不是自毁式的“硬刚”——显得干瘪而无说服力。
实际上,当“已回未支付”能比“劳动保护法”超前出现在热搜榜;当没有逻辑关系的花哨押韵、排比、咆哮和歇后语可以轻松扭转跑票形势;当辩手、嘉宾和导师因“辩题成不成立”说得越来越多之后;奇葩说的“以退为进”看起来更像是“以退为退”。
在这趟折返的路途上,“奇葩”还在说,但ta们很难再去回答一个真问题了。
02 消失的真问题
在最近接受《娱乐资本论》的访问中,《奇葩说》的节目监制李楠楠和记者聊到本季第六期“你支持推出前任点评app吗”这道脑洞题时,他说,
“其实这个题的前身更现实,叫‘该不该在网络上公开讨伐你的前任’。如果就这样讨论,它能够延展的东西相对比较负面。我们不希望讨论别人隐私,所以改成前任APP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架空的载体,但是它可以讨论更多,包括网络暴力、爱情回忆、科技发展等,这样就变得丰富起来了。”
对于节目组这样的选题逻辑,你会同时感到理解和诡异。理解的部分是,经过近几年的台上台下的“事故”之后,出于风险控制,《奇葩说》难免需要把控议题走向,让辩题不至于走向“负面”。诡异的部分是,把一个原本饱满的、来自于现实的议题阉割掉一部分(可能引致负面延伸的部分),再用架空的、虚构的条件去“丰富”它……一种类似于先晒干再泡发的操作?
但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奇葩说走到今天的常态。
网友所整理的《奇葩说》第一季部分辩题
如果你留心看,在《奇葩说》刚开始走红的前几季,辩题基本都是一个单句就可以说完的,每个辩题也都有一个相对宽广的指涉空间,能代表的身份和声音也更为多元。
即便把“该不该向父母出柜”和“好朋友可不可约”等被下架的辩题刨去,早期辩题中如“丑闻主角就活该被万人虐吗?”和“没有爱了要不要离婚”,放在今天也都是可以就问题来聊问题的话题。
但以上两个辩题再拿到如今的《奇葩说》,更有可能被替换成,“奇葩星球的丑闻主角不再被万人虐,我该不该移民”,又或者是“和伴侣没有爱了想离婚,我错了吗?”
七年过去了,《奇葩说》的辩题从单句走向分句,从现实走向虚构,其中的限制除了架空现实,缩紧辩题成立的条件,往往还要对辩题中的“我”又再进行一次界定。
无尽的界定、界定、界定,自然为了把控话题延伸的可控性。但随之而来的是,问题本身的价值也被逐渐削弱,“就问题讨论问题”变得极其不讨好。更多时候,选手要靠黄执中的经典句式“这道辩题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什么?”来进行对题目的升华或扭曲。
“辩题”变成了“前提”。真正要展开论述的“题目”到底是什么,每个人可以自由发挥。
臧鸿飞在本季《奇葩说》的辩论片段
臧鸿飞在这一季《奇葩说》的第九期的辩论里说起过自己送孩子去上学时的心情,“因为从小到大是你陪着他,但是他走进这个门,你就不能再挡在他前面了……你看着他这么矮,离拉歪斜走进校门,你会难过,因为他像世界上最矮小的战士……为人父母就是卑微”。他之所以要说这些,是为了打一个“家长群里大家都在吹捧老师,我要不要跟风”的辩题。
这种情感落实到具体个人是挺感人的。但在“家长退出家长群”已经上过热搜并引起多番报道和讨论后。辩手竟然还站不到教育系统问题的高度来指出症结,竟然能忽略教育作为单一晋升渠道给老师和家长带去的共同压力,竟然还是要靠打感情牌来证明普遍的跟风是值得做也有道理的。如果煽情这么管用,多数人都默认“娘道”和“父母为大”等一言以蔽之的“传统”道理,那所谓思辨和为长者背书之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所以在这一季,导师、辩手和弹幕里频频提到的“说得挺有意思,但和辩题有什么关系”终于沦为常态。
“真问题”消失了,“伪问题”没有探讨价值。那就搞笑吧。讲观点的方式,比观点本身变得重要。段子+价值+煽情成为了致胜公式。而当语言在一个主打思辨的节目里,终于沦为表演形式本身后,思辨和八股文之间的界限也不明确了。
有很多场外因素可以来解释《奇葩说》当下的部分尴尬,辩手型选手的流失、言论尺度的不透明和米未作为一家公司,最终也还是要考虑签约艺人的发展……但你是确实很难再想起一个“最初”的《奇葩说》,一个马东建议“40岁以上的人请在90后陪同下观看”的《奇葩说》。
而如果节目辩题、赛制和内容的变化能大致勾勒出《奇葩说》里的真问题是怎么消散掉的。那也可以再往前探一步再提问,为什么真问题会就这样消散掉呢?尤其当你曾自认为是马东口里的“90后”过,看的《奇葩说》越多,也许越能知道它的问题,可以是一个人的问题,也可以是一代人的问题。
03 再见奇葩,再见街头
《奇葩说》的走红是个被研究和写作了很多遍的故事,自媒体的报道、访谈和评论外,在知网上搜索节目的相关论文,能超过一百页。
在还没有多少人看过网综的时代,《奇葩说》的胜利确实是个新奇的现象,这也让它的出现一举道出了两种出现:网综的出现需要被看见,以及本不出现在“主流”话语里,但靠网络赋权后出现的一群人需要被看见。
“网生代”就这样成为理解《奇葩说》成功的关键所在。
狭义的“网生代”更接近于从小就能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90 后,再较真一点的话,绝大多数是 95 后。广义一点看这个概念,“网生代”也不必有明确的年龄界限,学院派的老师、专业化的辩手和作出主流价值外选择的人群……所有想要靠网络赋权开辟新表达空间的人或许都算,而这也基本构成了奇葩说的参赛辩手。
在这个基础上来看,五六年前《奇葩说》的走红,确实是天时地利,顺水推舟。
第一季《奇葩说》里的姜思达
PC互联网时代我们当然有过更加接近“乌托邦”的公共讨论空间,更深的讨论,更少的情绪。但那是几乎专属于程序员、大学生和媒体人的板面。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从2010到2015年的快速普及,人人、微博、豆瓣,甚至刚出现时期的B站抖音快手,才真正把野生于社会各角落的“奇葩”们打捞了出来。
《奇葩说》15年前后的现象级成功,实际上依托于这个“赛博街头”对公共话题的议论,对小众人群的展现,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但那也是这个“街头”最后的美丽光景。最近几年来,监管的压力,资本的逐利,让这片“赛博街头”的阴暗角落得到整改,旗帜和涂鸦被霓虹灯广告牌所取代,暗号和行动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交流形式,再小众的文化也都有了明亮的未来。
到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真正意义上称得上“社交媒体”的公共空间,实际上只剩下微博了——这也解释了《奇葩说》的大量选题都和微博热搜“撞题”的奇异巧合。
然而,微博热搜,这个我们唯一拥有的“公告牌”,真的就代表着一代年轻人对现实的理解吗?明星隐婚、私生和代孕等“远方”话题以情绪垃圾桶的形式长期霸占在这块公告牌上,但这些我们和真实的当下有多大关系?
《奇葩说》从七年前的闪亮登场,到今天难以再提出一个真问题的困境,有大部分原因或许正基于此:《奇葩说》从舞台上的人、选题,到舞台下的发酵、二次讨论、反哺生产,都依托于那片健康、蓬勃、包容的公共讨论空间。后者确定了前者是单一还是多元,是丰满还是贫瘠。
上一季《奇葩说》里的詹青云
而在今天,是的,我们只配得上第七季这样的《奇葩说》。
如果普遍来说,一个真实的现实已经难以被认识并达成共识,那要如何基于“真实”来提出问题。如果“奇葩”作为一个小众已经被看见了七年,那要如何基于此前被遮蔽掉的真实生活经验来提出问题。如果一个节目又想提出问题,又想制造话题,又必须惮于流量和影响力的反噬,那它除了去提出一个热搜榜上被争论和检验过了的问题,又有何他法。
项飚曾在《把自己作为一种方法》的访谈里提到过一种观点,大意是我们如今最大的问题不是说假话,因为说假话的前提在于,能知道什么是“真”,能知道“真”的标准和概念定义是什么。
套用一下,对于一个强调“思辨”的语言类节目来说,“思辨”的答案可以没有对错,但分不清自己是在“真思辨”还是在“装思辨”,这无疑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可悲的是,这样的问题可能连《奇葩说》自己也无法解决。